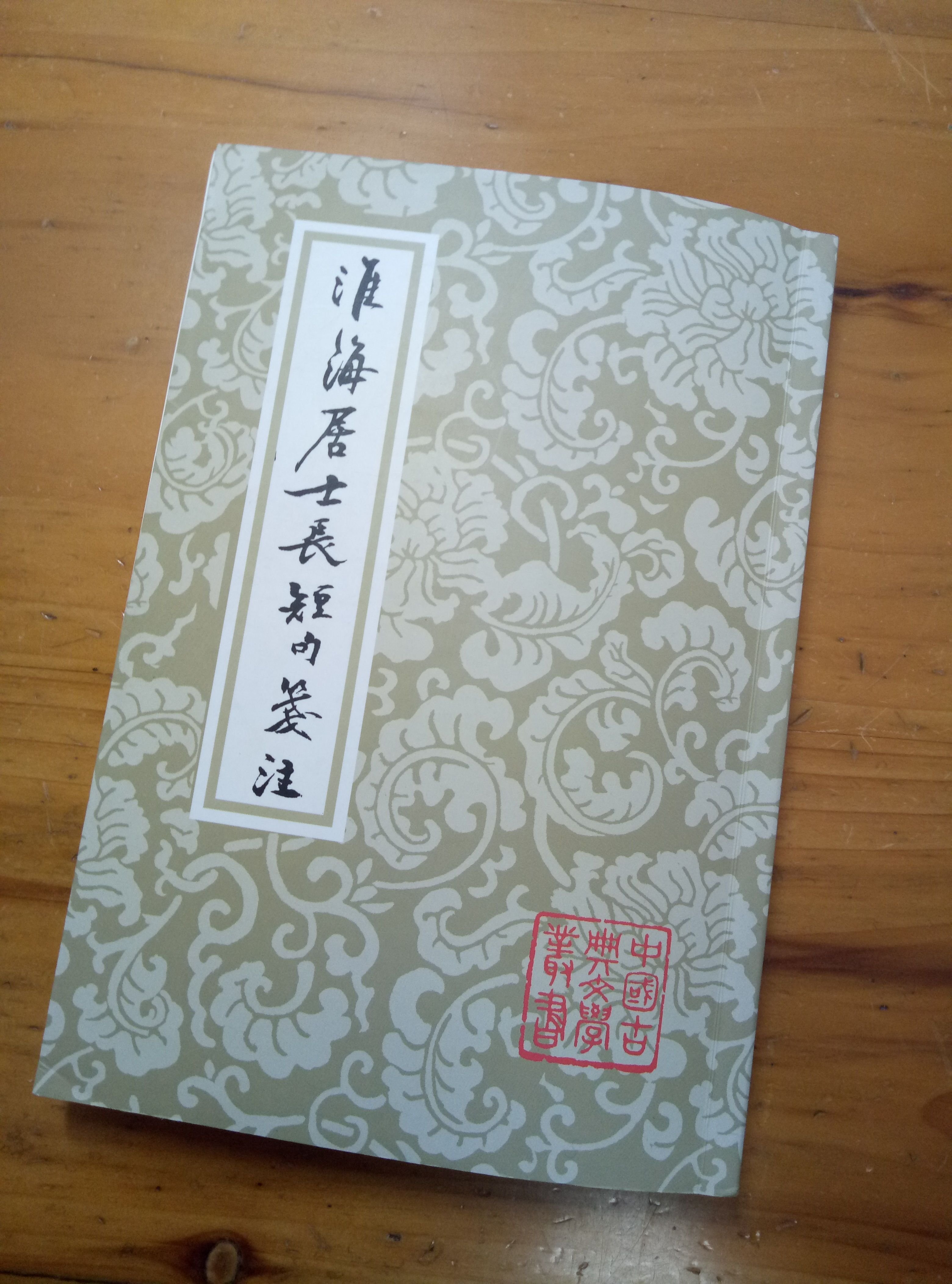
秦观家境不错,放在今天,算是中产阶级。一个家庭富足,生活优裕的少年——还是老大——难免胸怀大志。
大宋是一个造星、追星的时代。秦观为啥叫秦观?因为他爹秦元化公,年轻时候曾经在太学读书,师兄弟间有叫王观、王觌的,才华横溢,秦元化大为倾慕。古人常以自己崇拜的对象给子女命名,于是秦元化的长子、次子便唤作秦观、秦觌。
老爹搞“偶像崇拜”,儿子也差不到哪去。在《别子瞻》里,秦观写道:“我独不愿万户侯,惟愿一识苏徐州。”正是苏轼改变了秦观的一生。
秦观十五岁时,父亲过世;十九岁,与徐文美成婚。古人先成家,后立业。秦观成了家,自然要开始思量立业的事儿。其时正值神宗继位,励精图治,想要增强国力,在对辽、夏事务上有所突破。这种环境下,秦观也不想当个文弱书生,偶像正是大唐郭子仪、杜牧。
郭子仪武举出身,常年驻守塞外,节度西北。其人英武果敢,骄横奢侈,安史之乱中几经波折,吐蕃入侵时救急于难。
子仪乃外弛严备,中输至诚。气干霄而直上,身按辔以徐行。於是露刃者胆丧,控弦者骨惊。 ——秦观《郭子仪单骑见虏赋》
杜牧以文人之身精熟军事、长于策论,兼有忧国忧民、建功立业和伤春悲秋、鸿衣羽裳的气质。杜牧这种豪迈和华丽混合的特征亦为秦观所继承。
在文章言,秦观是壮志凌云的,一心以天下为己任,想的是“建事揆策,收复故地”。在诗词言,则前期绮丽纤巧,时人笑称“小石调”、“女郎诗”,甚至“如时女步春,终伤婉弱”;晚年屡经挫折,风格渐显沉郁厚重。
秦子曰:“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,愿效至计,以行天诛,回幽夏之故墟,吊唐晋之遗人,流声无穷,为计不朽,岂不伟哉!”——陈师道《秦少游字序》
既授受于先人,接下来便当亲自躬行。行冠礼时,表字“太虚”——也就是天空、宇宙。二十来岁,家室安好。秦太虚终于按捺不住,收拾行囊出门游历江左、寻访古迹,恰逢苏轼(时任杭州通判)名动天下。读博士生得找个好导师,士子游学自然也不能将就。秦观(家在扬州高邮)动了上门求学,求带飞的主意。可惜秦观无亲无故的,去的时候刚好苏轼不在,只得另做打算。
没多久,苏轼要去密州做知府,途经扬州,顺道拜访寺庙。哪知寺里墙上竟留有“自己”的笔迹!这可奇了,那年苏轼才四十岁,春秋鼎盛,总不至于自己写的转头就忘了吧。直到跟老朋友孙莘老说文论道时,孙莘老拿出一沓某位“青年才子”的佳作,苏轼细细揣摩,这才恍然大悟——“向书壁者必此郎也”。(这里面有暗箱操作吗?十分可疑!)
不管怎样,秦观总算是和偶像搭上了线。可惜古代交通不便,苏轼又远在密州(山东),只得书信往来,也颇有意趣。五年后,苏轼从密州调动到湖州(杭州旁边),秦观趁机陪游,唱诗和韵,好不痛快——即使分别之后,一年间佳作亦如泉涌。“山抹微云秦学士”便来自于年中一首《满庭芳》:
山抹微云,天粘衰草,画角声断谯门。暂停征棹,聊共引离尊。多少蓬莱旧事,空回首,烟霭纷纷。斜阳外,寒鸦万点,流水绕孤村。
销魂、当此际,香囊暗解,罗带轻分。谩赢得青楼、薄幸名存。此去何时见也?襟袖上、空惹啼痕。伤情处,高楼望断,灯火已黄昏。
——秦观《满庭芳》
可这年对苏轼来说却很不轻松。神宗力主变法,苏轼(旧党)便免不得在地方上调来调去,去湖州才三个月,就一不小心惹出“乌台诗案”——作为当代文宗,影响力巨大,某些新党人士视他为眼钉肉刺——被御史指为“讽刺朝政,妄自尊大”云云,差点没命。好不容易保住性命,苏轼心灰意冷,便一心属文,“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 ”。秦观三十七岁那年终于进士及第,步入仕途。可是新党执政,也捞不到什么官当。又决心改字“少游”,不是怀念二十来岁在外游历的时光,而是“ 愿还四方之事,归老邑里如马少游,于是字以少游,以识吾过 ”:
以前啊,我年轻气盛,跟杜牧似的“ 强志盛气,好大而见奇 ”,觉得功业好成,天下无难事。辽、夏对我国威胁大,我就想着把这俩办了。所以表字“太虚”,以存志、立足。现在呢,年纪大了,想法变了,搞不动那些了,只想学马少游归老乡里。故而改字“少游”。这便是陈师道作《秦少游字序》的由来。
神宗去世,哲宗继位(九岁),祖母垂帘听政。太皇太后老奶奶不喜欢变法,启用旧党,没几个月就把苏轼召还京师。不久,秦观亦被召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参加太学考试(由苏轼命题),结果一同过关。苏门学士,终于汇聚一堂、日日酬和。可新党不尽是好人,旧党亦然。相比王安石、司马光这样为社稷计的肱股之臣,大部分官员与其说是政见不合,还不如直说是争权夺利。苏轼看不过去,极力抨击——本来就不容于新党,现在又得罪旧党,结果可想而知——最后苏轼自请知杭州,总好过乌台诗案。门下学士们倒在京师悠游几年,编修国史、校检书籍。
这是秦观最得文学之乐的时期,京师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,相与唱和,其乐无穷。“金谷俊游,铜驼巷陌”,多是雅致盎然,兴尽而归。
梅英疏淡,冰澌溶泄,东风暗换年华。金谷俊游,铜驼巷陌,新晴细履平沙。长记误随车,正絮翻蝶舞,芳思交加。柳下桃蹊,乱分春色到人家。
西园夜饮鸣笳。有华灯碍月,飞盖妨花。兰苑未空,行人渐老,重来是事堪嗟。烟暝酒旗斜,但倚楼极目,时见栖鸦。无奈归心,暗随流水到天涯。
——秦观《望海潮》
未几,哲宗亲政,再次启用新党。苏轼、苏辙、秦观、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俱被贬,而且均为一贬再谪。就拿苏辙来说,知汝州,徙袁州,再谪筠州。苏轼甚至被发到海南去了。那年头,光是在这些地方跑路,就能把人累死,要是身体不好,水土不服,偶遇疾病,可真是有去无回。苏轼一生豁达,即使仕途不利,也能纵情山水;秦观不能,试举两词便知:
星分牛斗,疆连淮海,扬州万井提封。花发路香,莺啼人起,珠帘十里东风。豪俊气如虹,曳照春金紫,飞盖相从。巷入垂杨,画桥南北翠烟中。
追思故国繁雄。有迷楼挂斗,月观横空。纹锦制帆,明珠溅雨,宁论爵马鱼龙。往事逐孤鸿,但乱云流水,萦带离宫。最好挥毫万字,一饮拚千钟。
——秦观《望海潮》
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,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,杜鹃声里斜阳暮。
驿寄梅花,鱼传尺素,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,为谁流下潇湘去?
——秦观《踏莎行》
同为写景,前者意气风发,豪气干云;后者泪尽阑珊,杜鹃泣血,沉郁至极。如果说“春去也,飞红万点愁如海”尚能见春,见春才有愁可言;那么“郴江幸自绕郴山”已是一片虚无,无所谓春,无可期望,也没什么愁,唯沉沦而已。传言云:“东坡绝爱其尾两句,自书于扇。曰‘少游已矣,虽万人何赎’。”
皇帝还真是短命职业,哲宗没能活过秦观。一一〇〇年二月,哲宗崩。旧党诸位被赦,内徙。六月,苏轼和秦观相见,秦观给苏轼念自己写给自己的挽词。两个月后,秦观在藤州光华亭去世。
春路雨添花,花动一山春色。行到小溪深处,有黄鹂千百。
飞云当面化龙蛇,夭矫转空碧。醉卧古藤阴下,了不知南北。
——秦观《好事近·梦中作》
一生为情所困之人,最后在古藤阴下、在梦中、笑着步入永恒。我们实在无法设想更好的结局。
只是可惜,少游一生未作“少年游”。
檐牙缥缈小倡楼。凉月挂银钩。聒席笙歌,透帘灯火,风景似扬州。
当时面色欺春雪,曾伴美人游。今日重来,更无人问,独自倚阑愁。
——周邦彦《少年游·黄钟楼月》
